我在以前多篇文章中介绍过,在我数十年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生涯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帮助和影响过我的多位前辈和晚辈学者。我是一个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兄弟姐妹亲情之恩,夫人对家庭“服务”之恩以及众多前辈师长和晚辈学生朋友的提携与帮助之恩。此外,作为大学退休老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亲身感受到若干前辈师长的科学风范。有的老师虽然没有直接给予我具体帮助,但是他们的学术风范深深地影响了我,潜移默化助我学术成长。现在对于我们这些70开外的人,常常回忆这些温馨往事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将这些经历形成文字供学术晚辈们成长参考。
我是1970年毕业的,毕业时没有按时颁发毕业证书,更没有学士学位证,因为那时我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实行学位制度。1980年5月4日补发的大学毕业证是这样表述的:“学生刘庆生于1965年9月入本院(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学习金属与非金属地球物理勘探专业五年,准予毕业”,没有“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的文字表述。当时的红印和钢印都是“武汉地质学院”,那时我们已经被迫迁出京城定居武汉。我国高校1966-1968三届毕业生没有留校任教学生补充教师队伍。所以,1970年国家决定,在1969(在学校已经呆了六年)和1970两届学生中恢复留校学生任教,然而,对于我们1970届留校任教学生,大学五年期间只在1965年10月(整个9月新生练习队列走步,庆祝国庆节天安门前游行)至1966年5月期间学习了一些基础课程(期间还在张家口一个部队下连当兵38天)和1967年“复课闹革命”学习了几个月的基础和专业课程。显然,凭这点基础和专业知识,我们面临如何成为一个合格大学教师的严峻考验,为此我们这两届留校教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然,事在人为,毕竟在大学任教学习条件很好,教师资源和图书资料丰富,只要肯学习,完全可以弥补之前学业上的损失。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了有利学习条件,我们勤奋刻苦努力,最终成为了合格的大学教师。我是在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岗位上退休。
显然,这里介绍的多位学者和老师只是帮助和正面影响我的众多学者代表,有的前辈师长另有专文介绍(怀念我的前辈师长谭承泽先生,向老一辈科学家涂光炽先生学习,感受九三学者风采)。这些学术前辈的学术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感染和影响了我。以至于时隔多年依然能够清晰回忆起当年的许多温馨场景。按照时间顺序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位是大学期间的物理老师蒋智先生。蒋老师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50多年过去了,至今脑海里依然能够清晰记住他那严肃的面部表情。他的物理课讲得非常精彩,除了讲授普通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外,在课堂上蒋老师常常强调我们学生在学习中要“多思”。由于蒋老师“多思”的话说的多了,以至课下我们班同学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多思”老师。也许有的同学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称谓而已,而我却将蒋老师的“多思”教诲铭记在心里。“多思”成了我长期以来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习惯思维。无论参加学术会议,还是阅读科技文献以及与同行交流,都会主动“多思考”,将别人的先进知识和思维方式通过“多思”变成自己的科学研究行为。
第二位老师是国际著名矿物学家彭志忠教授。彭老师195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即随清华大学地学系师生一起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因测定出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破格晋升副教授,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彭老师来到刚成立的湖北地质学院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我毕业留校时也分配到那儿成为一名“新工人”(据说是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的“发明”,以区别于产业工人)。在那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彭老师和另一位物理老师张国雄先生(195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共住一室。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每周只能吃到一次肉。我和另外一位留校老师住在彭老师前面一排平房的一小间。因此,我经常到彭老师那儿聊天,感受这位学术大碗的工作风格。当我看到彭老师书架上满满的专业外文书籍时,我很感慨。因为,当年大多数年长教师并没有将这个校办地质队当成长久工作场所。所以,一般随身只带了一点基本的教学参考资料应付而已。事实也是如此,这个“校办地质队”只存在两年,1972年我们重新迁回北京。当时看那状态,似乎彭老师准备要在丹江长期呆下去。其实不然,与书相伴已经成为了彭老师的“生活习惯”,大有“人在书在”的气势。有一次,我问彭老师,这么多外文书籍应该会有不少属于作者赠送的吧,他认真地对我说,“不,那是我花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钱)买来的”。即使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彭老师依然坚持科学研究,从杨家堡含钒较高的煤层中发现了两种新矿物。在上世纪80年代他还提出“矿物的准晶结构”观点。有人告诉我,彭老师看到我国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黄汲清先生的一本专著,由于这本书已经脱销,彭老师居然从图书馆借来抄写一本留存,这是何等高尚的“求知若渴”精神。令人惋惜的是彭老师由于罹患重病没到古稀之年就英年早逝。在如此简陋条件下,彭老师依然乐此不疲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这种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精神一直激励我克服困难奋勇向前。
第三位是数学老师兰仲雄教授。1972年,高元贵院长鉴于当年学校点多(在湖北有江陵,汉口,丹江)影响办学向中央报告,建议撤销江陵和丹江教学点,学校师生在武汉汉口原地质学校和北京原校址相对集中办学。中央批准后,我们从湖北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迁回北京。当年地球物理勘探系领导组织我们这些留校人员“补课”,开设了数学、物理、外语及专业等课程,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数学老师兰仲雄教授。他是1952年从清华大学过来,据说是华罗庚先生的门生,是北京地质学院数学教研室首任主任。兰老师一口福建口音,教学中体现的学者风范至今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兰老师上课基本没有讲稿,然而内容娴熟,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照本宣科。他的精彩课堂教学风范在我心中埋下了要做一个优秀教师的种子。
第四位是数学老师李锦才教授。印象中他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广西大学。李老师来自广西农村,夫人没有工作,是一个“全职太太”。李老师家里子女多,全靠他一个人工资负担,生活比较困难。为此,李老师后来调入家乡的桂林地质学院(即桂林理工大学),以求解决孩子就业问题。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李老师依然坚持将数学与地球物理专业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重点与地磁学相结合。我曾经完整跟班听完他给1976级学生主讲的数学课程。当年,像我们这样的行业特色大学,基础课部的数学老师一般不做科学研究。1987年我第一次给地球物理专业学生主讲磁法勘探课程时由于教材中涉及较多的数学公式,其中有三个公式推导较难没有把握。我及时请教住在隔壁楼的李老师,请他为我把关。几天后,李老师答复我,我这三个公式的推导没有问题。李老师在家庭生活困难条件下,自觉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令我钦佩和感动。那时没有科研经费支持,他完全是“自讨苦吃”做自己喜欢的科学研究。我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做科学研究的乐趣,是我与后辈谈论科学研究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
第五位是我国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马杏垣教授,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硕士生导师。马老师1948年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后来长期任教北京地质学院,曾任副院长。文革结束后调到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工作。我的文章:“回忆30年前得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帮助”说的就是他帮助我的故事。马先生属于我国大地构造领域的“少壮派”。在此之前我国地质科学界已经拥有了五个享誉世界的大地构造学派:陈国达的“地洼”,张文佑的“断块”和张伯声的“波浪状镶嵌”,黄汲清的“多旋回”和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然而,马先生学习前人但并不照搬,他的科研团队依据河南嵩山地区多年科学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伸展构造”学派。马先生的“不唯上”,“只唯真”的科研创新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第六位,第七位分别是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王鸿祯先生和岩石学家池际尚先生(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常怀念的一位老师)。我们1972年从湖北丹江校办五七地质队迁回北京时与王先生和池先生同住在学12楼三层。王先生家住东头一大间和北面一小间。王先生1947年博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50年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1980-1983年出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王先生不苟言笑,表情严肃,虽然同住一层楼,我们这些物探系的晚辈似乎没有人和他说过话。王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高大上”的严谨科学家。他的“三不作序”原则(非自己专业范围著作不作序,没有阅读文稿不作序,不用作者提供的序言初稿,自己撰写)体现了他的严谨学术风范。据说年过70还坚持出野外带学生,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池际尚先生硕士博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她住在我的隔壁。池先生待人极其随和,没有一点学术大腕架子。休闲时间池先生偶尔还和我们物探系留校的几位晚辈打扑克牌。多年来没有看到两位先生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两位先生的“低调务实”和“潜心学问”学术风范和品质深深感染了我。
第八、九位是师生俩,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仪先生和他的学生殷鸿福先生。杨先生1939年博士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除了学术成就辉煌,他的英文非常棒。据说文革结束后不久,一个地矿单位希望将一些科研成果资料翻译成英文向国际同行传播,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专业英文翻译人才。后来托人找到杨先生,然而当时英汉专业词典很稀缺,难倒了地矿单位有关人员。杨先生听说后告诉接待人员,不用找词典了,你们只管将科研文字材料拿来就行,他的专业英文水平惊呆了相关科研人员。杨先生博学、多才,乐于助人,他总是一副慈祥善良的老人形象,对人谦和,尤其对我们后辈,有求必应。那年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因科研需要电话联系,我的英语口语无法应对,只好请杨先生出面,当时杨先生已是80开外的耄耋老人,他听了我的解释后立马说,我帮你说去,顿时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殷鸿福先生是杨先生的硕士研究生,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科学精神深得杨先生的嫡传,他俩是学校国家级“地层古生物”团队科学传承的第一、第二代标志性人物之一。殷老师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我在文章:“回忆我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Hansen教授合作”中详细记述了他们师生俩推荐和帮助我与Hansen教授科研合作的经过。他们是我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的“启蒙老师”,我对他们始终心存感激之情。杨先生和殷先生在学术上帮助后辈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后来对于年轻人的学术需求尽力满足的精神来源。
第十位是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许厚泽院士。1997年我晋升为教授,1998年我申请博士生导师。然而由于我在系研究所长达8年,没有给本科生上课,所以一直没有招到硕士研究生。2000年,我将代表性成果提交中科院测地所,申请他们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记得那天,许厚泽院士看完我的材料后高兴地说,小刘,你的成果不错,我们这儿争取先给你博士生导师资格。不久后就将聘任我为中科院测地所“固体地球物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的“红头文件”颁发给我,同时,中国科学报发布一年一度中国科学院博士生招生导师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我将红头文件扫描件发给时任校长殷鸿福先生。他表示祝贺。此后,我没有辜负许老师的提携和帮助,我在测地所指导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已经成长为大学教授。
第十一位是杨巍然教授。杨老师是我国大地构造学的少壮派人物之一,是马杏垣先生大地构造科研团队的骨干成员,曾经跟随马先生多年。杨老师依据秦巴地区长期研究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开合构造体系与构造运动”观点。1986年杨老师出任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杨老师待人谦逊,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总是给予热情帮助。至今记得1986年我随他去秦巴地区野外地质调查一个月的温馨场景。杨老师用通俗诙谐话语告诉我野外地质构造调查“套路”:远观近瞧,左顾右盼,敲敲打打。我向杨老师学习的地质知识为我后来从事“大陆下地壳岩石物理研究”方向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十二位是罗延钟教授。罗老师是我国电法勘探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罗老师除了出色完成教学任务外,坚持科学研究,并在美国SEG出版了一部英文专著。他是我们物探系上世纪30后出生的老一辈教师中科研成果丰硕的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湖北省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在我校召开。在这次换届选举开始前他在会上建议,理事会应当增加年轻人,并提议我作为额外的候选人。理事长许厚泽院士当即表示同意,投票获得通过,使我意外当选。事情虽小,却体现了罗老师和许老师对我等晚辈的充分信任,鞭策我学术上努力向前。
诚然,除了上述介绍的几位前辈老师外,还有诸多后辈学人对我学术上一直给予大力帮助。例如高山教授,我的两篇文章:“我谈高山院士的科学精神”(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16年第3期),“我与高山院士的交往”(今日科苑2016年第7期)介绍了我们数十年来相识相知合作科研的故事。对我学术影响较大的后辈学者还有:长期合作科学研究的岩石学家郑建平教授;我的本科学生地球物理学家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青松和中科院测地所汪汉胜研究员及我的研究生刘振东教授、罗银河教授、杨涛教授、李海侠教授、付媛媛研究员和乔庆庆研究员等。这些晚辈学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勤奋刻苦,学风正派,在自己的岗位上潜心做自己的科学研究。这些前辈师长和晚辈学人的科学风范始终是我科学研究内心动力和教育晚辈的好素材。
2018年8月1日初稿,8月10日完成,2019年3月25日修改,2020年12月18日再次修改。

湖北省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合影,许厚泽院士(前排中)、作者(前排左一)在会上当选为理事(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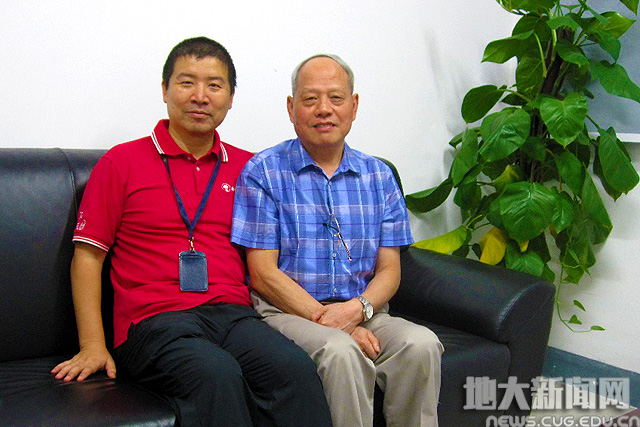
1993届本科毕业学生刘青松教授合影(2017)
作者简介:刘庆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我校前身)地球物理勘探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我校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我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地球科学”中英文版与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in China 编委(Springer出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SEG)会员。(编辑肖潇 特约编辑徐燕)